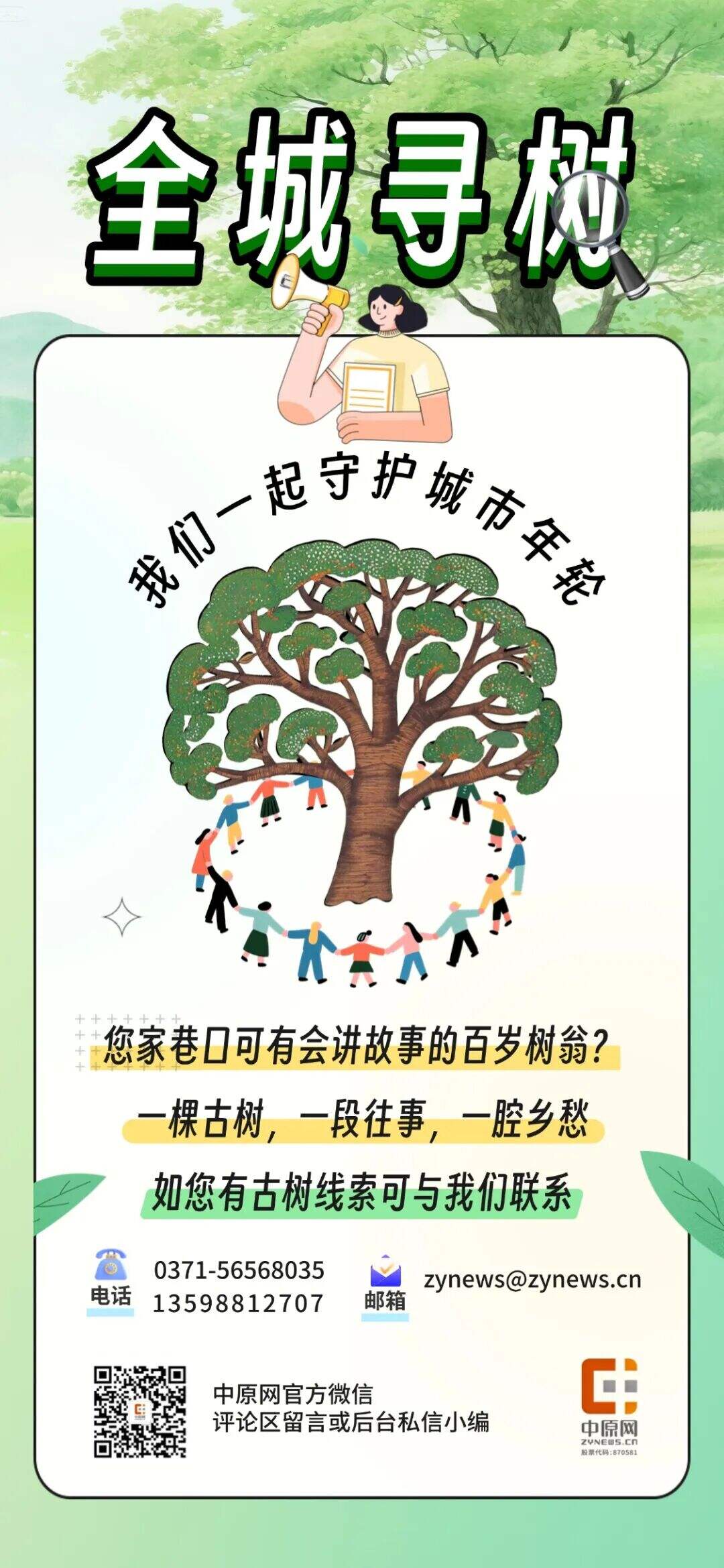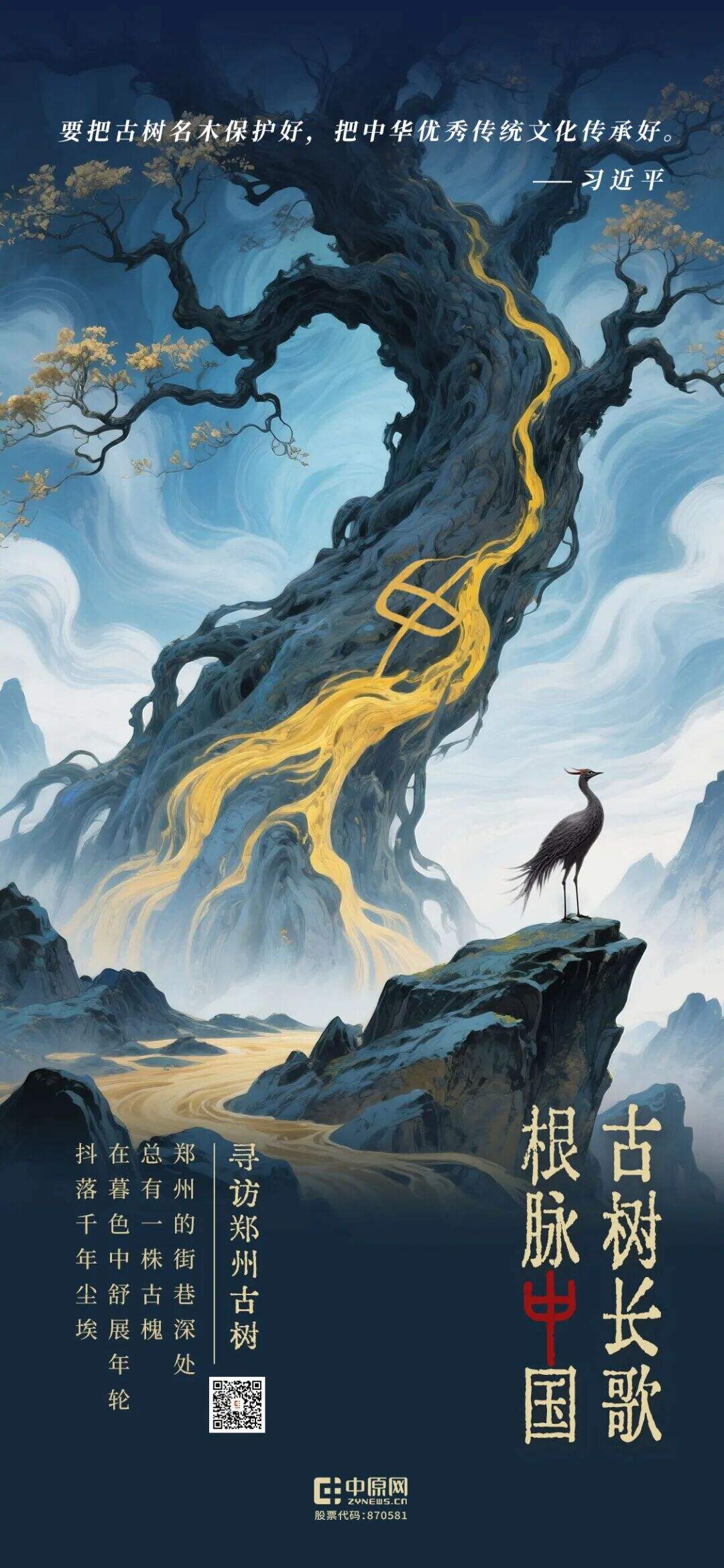
“这里就是当年祖师庙的位置,从四棵古树中间走过去,就抵达庙址了。”七旬老人时永福站在广场上,双手比划着向我们还原记忆中的原貌。他的声音温和细缓,作为《郑州上街区夏侯村时氏文化志》的主笔,他对这里的历史如数家珍。
雨后的古柏更显苍翠,深褐色的树皮因湿润而泛着光泽。老人走近轻抚着其中一棵古树:“有时候很神奇,在这树下散步,仿佛能穿越时空,感知到明朝嘉靖年间,我的祖辈时源左都督在此养病的情景。”
在时永福身后,四棵侧柏站得方方正正,间距不差分毫,它们的前方正是夏侯村祖师庙旧址。这长在上街区金华路中段的古柏,打明嘉靖年就扎在这片土地上了,算到如今已有455岁,被列为郑州市二级保护古树。

△如方阵一般站列的古树
四棵古柏站成个方方正正的阵,像支不动的仪仗队。西边那棵的皮最糙,鼓出的纹路像老将军暴起的青筋;东边那棵却温和,树皮叠着云片似的,雨珠挂在缝里。它们比夏侯村后来的许多故事都早。
“原先这庙叫始祖庙,咱都喊东大庙。” 时永福的长辈曾告诉他,始祖庙也叫祖师庙,位于夏侯村东头,也称东大庙。相传,这座庙建于明朝后期,历经多次扩建,到清朝中期,庙宇已有相当规模,仅建筑群占地就有约2000平方米。整体为灰砖灰瓦建筑,雄伟壮观。
曾经香火鼎盛,庙里的大钟上刻满了捐资铸钟的夏侯族人姓名。1954年,庙宇被拆,但四棵柏树却保存了下来。

△参天古柏
“小时候,这里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。”时永福说,夏天人们在树下乘凉聊天,孩子们围着树追逐嬉戏,过年过节时村民会在树下祈福。那些日子,就像发生在昨天。

△系着红绸带的古树
时永福最爱蹲在树下给孙辈讲故事,话题总绕不开一个谜:“咱村叫夏侯村,可满村没一个姓夏侯的,你说怪不怪?”
“老辈人说,这里是夏侯惇安置伤兵的地方。”时永福说起村里的传说——三国时期,夏侯惇兄弟在此与敌军交战,伤员被安置在村东南的一条沟中养伤。后来轻伤员归队,重伤员痊愈后无法归队,便在此娶妻生子、定居下来。因为是夏侯惇的部下或后裔,故将这里命名为夏侯村。

△古树发新芽
也有说法认为与秦末刘邦的大将夏侯婴有关。“不管是哪种说法,都说明咱们村历史久远。”时永福笑着说,这些传说就像古柏的根系,深扎在每个村民的心中。
村里姓时的占了六成,时永福的祖辈时源,明朝时还是左都督,据说就曾在祖师庙旁养过病。“说不定他也在这树下散过步呢。”时永福笑着说。

△古树名木保护牌
2012年,夏侯村拆迁的消息传来,时永福和村民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四棵古柏。
“存在的时候不觉得,失去的时候倍感惋惜,古树一旦被损坏,就真的再也弥补不回来了。”时永福说,村民们像保护亲人一样守护着古柏,再三向开发商提出必须保护好这些古树。
令人欣慰的是,开发商特意在古树四周挖出透气孔,上面铺上木板,为古柏留出了充足的生长空间。今年春天,时永福欣喜地发现,古柏的叶子比以往更绿更茂盛了。

△古树透气
“村子拆迁了,但根还在。”时永福说,每逢传统节日,总会有村民回到古柏下,聊聊家常。年轻人外出打工,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来看看古柏;谁家有了喜事,也会到树下报个喜。
“我们这个村子,年轻人几乎都出去了,就剩下我们这些老人家守着。”我们明白,这四棵古柏也是他心里的“老人家”,陪着夏侯村人走过一辈又一辈。

△古树周围景象
如今的四棵古柏,站在商业广场中间,倒比从前更热闹了。
下午四点多,陆续有居民来到古柏下。老人们下棋聊天,孩子们玩耍嬉戏,年轻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在树下散步。四棵古柏静静伫立,见证着新时代的烟火气息。
“现在天天能见到它们,真好。”时永福说,只要古柏在,夏侯村就永远在。它们不只是一棵树,更是一座村庄的记忆,一代代人的乡愁。

△古树如高楼
夜幕渐渐降临,广场上的灯一盏盏亮起。时永福慢慢走回对面的新家。
他回头最后望了一眼古柏。在雨幕和灯光的交织下,四棵古柏的轮廓显得格外深邃。
新的一天,这位七旬老人还会准时出现在古柏下。而古柏,依旧以它们的方式守护着这里——见证着孩童长成少年,见证着新邻变成故交,见证着寻常日子里的每一个温暖瞬间。
这就是生活最朴素的真相:有些守望,注定要穿越更长的时光;有些根脉,早已在变迁中生生不息。